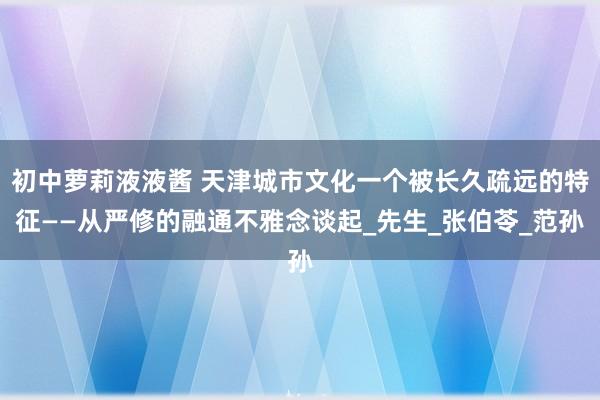
拿起严修先生,总嗅觉在他身上,有两个出入相随的标签,一个是“新”,一个是“旧”,但不知为什么(或出于皮相之见),阿谁“新”标签,却老是被特意意外、有形无形地淡化,而阿谁“旧”标签,却被特意意外、有形无形地强化了初中萝莉液液酱,致使固化了。
李冬君阐述在她的《严修与近代新私学》一文中这么问说念:“周恩来曰:旧社会的一个好东说念主。张季鸾曰:旧期间的一个完东说念主。缘何王人以‘旧’来论先生?以新旧论,是论故东说念主,并不论历史东说念主物。百岁之后,怎样论先生?先生之至当天,其东说念主已旧,而其命维新。近代开埠以来,西学涌入,校正、维新和新私学,成为新期间支点,天津首当其冲,范孙先生开民风之先,创办了南开新私学。何谓‘新私学’?以期间言,乃近代私学,非古代私学;论取向,乃洋化之私学,非传统之私学;其形势,乃私立学校,非私塾也。”在此,我要提请属目:在这个新私学的创办中就有张伯苓了,要是莫得张伯苓,就是家塾,有了张伯苓就是新私学了。缘何见得?算作第一作者,李冬君阐述还写了另一册书,书名就是:《想想者的产业:张伯苓与南开新私学传统》。
旧年年末,梁吉生阐述从好意思国通过微信发给我天津南开中学发布于2023年10月17日的两个晓谕——其一,庆贺天津市南开中学建校119周年,其中有这么的话:“天津市南开中学于1904年由爱国教育家严修创办,爱国教育家张伯苓为首任校长……”其二,喜迎天津市南开中学建校120年华诞,其中有这么对话:“南开中学于1904年由有名爱国教育家严修创办,聘有名爱国教育家张伯苓为校长……”但是,查察天津南开中学校史扣问中心编订的《天津南开中学史》(东说念主民出书社2015)一书,孙海麟先生在序言中写说念:“天津南开中学创立于清光绪三十年,即公元1904年,是由爱国教育家严修、张伯苓创办的。”第一章媒介:“南开中学创办东说念主严修和张伯苓就是基于甲午退让的刺激,果决遴荐在清王朝体制外兴办教育,以开办私立中学堂……”历史上的这段“说念义相劘,肝胆相许,志同说念合而患难相扶捏”的合营也曾似水如鱼,并且史有定论,今天,咱们不是应该对这种精诚合营加以传承并进展光大吗?为什么还会有对胡适所谓“竣工”的合营特意意外地切割呢?
张开剩余79%所谓“旧期间的完东说念主”出自张季鸾援笔的大公报社论《悼严范孙先生》,应该说,张季鸾对严修先生的评价是好的,是很高的,但行文却纠结于新旧古今先后之间:“迹其狷介自捏之处,固有类于独善其身者流,非当天所宜有。然就昔日东说念主物言之,严氏之捏躬处世,殆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东说念主!而在功利主义横行中国之时,若严氏者实不失为一鲁灵光,足以风示末俗。严氏其足为旧世纪东说念主物之临了模子乎!在吾东说念主联想的新东说念主物未始出现以前,对此成熟典型,自不成无恋恋之私,有心世说念者,或将与吾东说念主抱同感欤!”我不知说念我算不算一个“有心世说念者”,但我合计,严修先生“狷介自捏”自然,“独善其身”则否则,冒死奏开经济特科,发戊戌变法之先声,何“独善”之有,更谈不上“非当天所宜有”。不论是旧世纪,照旧新世纪,“在功利主义横行中国之时”,严修先生就是“联想的新东说念主物”!并且,我还认为,严修先生算作一个“新东说念主物”,其“联想”之处在于好像深化融通新与旧、古与今、同与异之间看似对立的联系,泄漏了大方法、高田地。用严修一又友邓庆澜的话说就是“益见玄妙之量为不可及也”。
有名记者、作者亦然学者的曹聚仁在1947年写过一篇著作《读严范孙诗》,其中,援用了王守恂先生在《严范孙先生古近体诗存稿序》中颇特意味的一段情节。王守恂先生言说念:“一日与范孙漫谈,范孙笑而问曰:‘今东说念主尚新体诗,曾见有工新体者谓我诗颇与新体近之,是何说也’守恂笑而答之:‘此无他,公之诗情真、理真、事真,不牵强、不假借、不暧昧、不涂饰,如说念家常,质料光明,精神恢弘,能造此境,又何新旧之殊与古今之异’”
接着,曹聚仁先生说:“这番论调,和其时新体诗的认识,如黄遵宪、梁启超诸东说念主所谓“熔铸新联想以入旧格调者”完全迎合;换言之,这即是期间的气味,说念虽不同而同趋于一个标的的。”曹先生还以记者的眼神、作者的笔触写说念:“严老笃行正人,而诗多意思意思,杂以俳谐。其《游意大利邦淠古城》诗:“平生不入平康里,东说念主笑拘墟太索然。当天逢场初破戒,好意思东说念主去已二千年。”末句出东说念主意表,读完不觉发笑(邦淠城中有二千年前之勾栏在焉)。他到底喝过墨水,吃过面包,呼吸过欧风墨雨的,勇于吸收新意境,遣使新词语,哄骗新语法,不受旧诗律的拘牵与旧意境的管理,勇于逃出如来佛的掌心翻斤斗的。”其实,这亦然严修先生拘与放的融通。这种融通,即使在他还莫得“呼吸过欧风墨雨”之前就决然存在了。
严修先生在贵州作学政时有一篇《谕贵州学子》,有句:“经济之学,中西并受。中其十一,而西十九。”不但建议中西交融,比例还十分安妥。
1909年,严修先生作《五十述怀》诗:“恶风卷海潮横流,秦越相携共一舟。何屑升千里谈宠辱,莫缘同异定恩怨。”不要把异同——不论是大同小异照旧大异小同——对立起来,同则恩,异则仇,实属“恶风”。
1922年,严修先生在《寿林墨青六十》诗中明确论证了我方的融通不雅念:“新学与旧学,交攻如对垒。我想毋庸然,实事但求是。……论文更聚讼初中萝莉液液酱,文言或语体。我想宜并存,毋庸相丑诋。”
严修先生的这种融通不雅念历来不被东说念主温煦,尽管与严修先生同期代的同道有过屡次揭示。当年,严修先生因成立崇化学会即被东说念主贴上“旧”的标签。严修在一首诗中戏弄说念:“当日被嘲新家数,而今复笑须生谈。只因国粹当存古,未肯主义变指南。”其中的“存古”要是佐以华世奎给严修的诗句“君有雄怀勇作新”,则可见“存古作新”在严先生那亦然融通的。而严先生的一又友陈宝泉则在《严先惹事略》一文中平直论说念:“盖鉴于国粹日替,姑为拨乱为治之谋,与当年之提倡新学,其精心正无以异。”
与严修过从甚密的藏书家卢弼在《严义冢碑》中写说念:“……锐意兴学,颛(专)以启钥民智为己任。……要之,先生兴学之念,在野在野无殊也。”看,又一个融通!在临了的铭文里还有两句:“适莫胥化,新旧兼融(适莫:心之所主为适,心之所否为莫,胥:总共)。”
王斗瞻先生的《天津严范孙先生听说》中也有这么的强调:“于阐发民族精神中,融积攒会,期窥东方文化之全貌,而为诞生新文化之基础。”
从历史上看,严修先生不论在轨制蜕变、教育改制、文化校正诸方面,对中国尤其对天津都有着遑急的影响。但是,这种影响跟着技术让咱们与严先生越来越远,也越来越淡了。比喻,严修先生的融通不雅一方面是中国传统中“自然日月星辰之昭布,山川草木之森列,莫不系焉覆焉,王人一气周流而融通之”(宋濂),亦即“大东说念主者寰宇万物为一体”的文化检修下酿成的,亦然对天津独到的地缘政事、经济、文化真切相识感受体验下强化的。
缺憾的是,咱们自后东说念主,对天津的这种地缘特征却作念了矮化的遴荐。咱们难忘住沽与河,却淡忘了海与洋。咱们长久在民俗的层面进行挖掘,却很少在民国的层面进行拓展。
举个小例子。上海的字画家一般会在作品上题名书于或写于“海上”,而天津的字画家一般会在作品上题名书于或写于“沽上”,一个海,一个沽,其落差太大。这种落差还体咫尺体裁创作上,上海从《子夜》到《上海的清早》再到今天的《似锦》,而天津却是《三寸小脚》《俗世奇东说念主》《蛇神》等所谓津味演义。
上海艺术家韩天衡,在书道尤其电刻上有荣华建树。我虽然不是很赏玩他安静野逸的格调,但他说的一句话,我却相配钦佩,他说:“艺术创作不是登山,而是登天!”哈!上海东说念主不但要把持“海”,还要把持“天”,而“天”与“海”历来不也都是天津的专利吗?
说到天,咱们记住的是“皇帝渡口”,(哪来的皇帝)为什么不是“天之渡口”呢? 些许年前,有东说念主建议天津要成为都门北京的“天堑”。其时我惊呼“我的天哪!”这是典型的顶点门户之争(只关门,不开门),虽然有所“卫”,却难有所“为”。而严先生是奈何说的呢?在《六十自述》诗中严修写说念:“茫无畔岸身家国,富饶领土亚好意思欧。”在严先生的寰宇里,莫得畔,莫得岸,莫得限,更莫得堑!
其实,天津和上海的地缘特征除了物理规模稍小稍大以外其内容是相同的,其所酿成的地缘文化也应该是一致的:河(江)海交织的地缘特征塑造通达、包容的气质以及“敢为六合先”的冒险精神。但是,咫尺一般的说法是上海是具有“海派文化”的前锋性,而天津则惟有“津派文化”的兼容性,恕我直言,假使天津真实不具备“前锋性”,那咱们就连“兼容性”,也保不住,也早丢掉了!
午夜伦理伦理片在线观我稍稍属目了一下,严修先生在他的诗文中较少提到“沽”,著作偶属“津门”,大多属“天津”;诗聚集偶有“七十二沽”“津沽”字样,而更多的是山、海、天。
请看严修诗《戏作示福士》(福士德太郎):“百万星球地居一,四分且让水三分。棕黄口舌总同种,南北东西何足云。……争存物竞惟恐定,至竟终须合大群。”“百万星球地居一”说的是什么——天!“四分且让水三分”,说的是什么——海!站在天与海的层面,智力有大融,大通,大同的田地,智力作念到“至竟终须合大群”。
晚清直隶按察使天津兵备说念周馥(谥悫慎,周学熙之父,周叔弢祖父)在天津毕命,严修撰周悫慎天津祠堂碑记,诗曰:“龙在天兮鸿在渚……奠河海兮永终古。”一件事,两句诗,河、海、天以及历史、咫尺、畴昔,尽在其中。
如今,咱们很有必要重温严修先生朝天向海、上六合海,登天追海(天津系退海地)的融通不雅,从头创立(还原)天行海运,天外海阔,天容海纳的“津派文化”,掀开门户,不仅京津冀,并且亚好意思欧。前不久,听说市政府要周转津湾广场,厚爱想象缱绻的机构碰巧与我相识,邀我参与辩论,我以为津湾广场周转需要一个魂,我提了两句话,那就是“天上之津,六合之湾”。这个魂,就是严修先生的魂。倘若获得了招供。希望那不单是是一句标语。
临了,我也不得不说(承认),登天难,蹈海险。但是咱们不成健忘严先生在24岁写下的粗豪诗句:“女儿胆气须雕塑,要向风坡险处行。”(诗集第一首)并且,这不是严修先生年青气盛之作,或敲敲诗钟,他终其一世都是那么作念的,亦然那么想的。请看,严修先生于1929年即生命临了一年写的临了一首诗(除自挽诗)有这么几句:“过眼几回苍狗白,惊东说念主一吼睡狮醒。大愚奈我聋兼瞽,惟有终生谢不灵。”(和曹蘅江亭诗韵)严修以及张伯苓列位先贤的维新想想、融通不雅念和历史算作,足以惊天荡海,也一经惊天荡海。
咫尺,该看咱们了!
(在“启智天津:教育与津派文化”学术计议会上的发言初中萝莉液液酱,南开大学,2025)
发布于:天津市